贾樟柯:最重要的不是历史,是人
煤矿工人韩三明从山西来到三峡,寻找他十六年未见的前妻。当摩托车司机带他来到「四川奉节县青石路五号」的时候,两人面前只有茫茫江水。司机指着水中间一片长草的小坡,说,喏,就是那里。外地的韩三明一脸迷茫,本地的司机却露出习惯性的嘲讽:你没看新闻啊,三峡工程,都淹了。
这是贾樟柯在威尼斯赢回「金狮奖」的电影《三峡好人》。用导演自己的话说,这片子吸引西方观众和导演的,并不是三峡工程的背景,而是三峡的人。即使两千年的古城两个小时就被拆毁,但城墙倒塌的回声,仍然迅速淹没在每个居民平淡的新生活里。镜头前的每个百姓都有看来比生活巨变更重要的个人选择。
有批评认为电影淡化了三峡工程的影响。贾樟柯自己这样解释:「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历史本身,而是历史中的人。拿奖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,因为我银幕上那些人受到尊敬了。他们是最重要的,他们的爱情、命运、选择是最重要的,但在中国,这些人们都被遮蔽掉了。」
亚洲首映礼上的贾樟柯,简单的黑T恤,匡威鞋,打招呼时候一团和气,笑容温和得好像绵羊。而一旦进入谈话,言语之间的坚定和自信,却让人对这个年轻导演,不得不肃然起敬。就像国外导演评价的,在他身上,也许真的能看到中国电影未来的希望。
问:以三峡工程为背景的电影,一九九六年曾经有一部章明导演拍的《巫山云雨》,十年过去了,你们拍摄的三峡,变化在哪里?
答:《巫山云雨》到《三峡好人》,是两个历史阶段。《三峡好人》时候的三峡工程,已经结束。整个中国从七八十年代以来,改革的大的变革格局也已经基本固定了。拍电影十年,我一直在拍一个变化中的中国,这个变化中有很多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。到现在的《三峡好人》,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应该务实的时代。这个务实就是说,变革所带来的资源的重新分配、利益的消耗已经趋于完成,就像这个工程一样,留下的只有过去巨变的蛛丝马迹,你可以感觉到变化里面每个人被社会影响的程度,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,或许这个完成,已经接近结束。
问:人们常常评价你的电影是小众电影,你自己怎幺看?
答:我一直承认我的电影在观受面上有局限,它不是娱乐类型,我也不期待能有一亿的票房,但它会有一个固定的观众群。比如《世界》,在中国票房只有一百五十万,但正版DVD有三十万张的销量,海外市场单是北美就有四五百万美元的收入,要看总收益,我的电影在中国肯定排前五位。而且我觉得,电影的文化作用不在于能被多少人数来左右。八十年代,《黄土地》全国只卖出一个拷贝,但它日后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。那时候上海还有一部电影叫《喜盈门》,两毛钱的票,全国票房一亿多,你说它有多少人看?但是时过境迁,就没有什幺价值存留了。
问:你的电影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命运,他们其实是中国的最大众,但是片子放出来,却成了小众电影,这本身不矛盾吗?
答:不矛盾。你知道为什么吗?从今天中国观众看电影的情况来看,电影已经不是一个大众艺术了。本来电影消费应该是无意识消费,就像我买瓶矿泉水,我渴了我就买了。但是现在看电影价钱不同啊,在北京,一家三口,再加小孩儿吃点东西,就好象看歌剧一样了。票价让这个艺术已经不是很大众化了。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大众在哪?中国最多的大众在哪儿?在城市之外,在小城市,在县城,在农村。但那里根本没有银幕。比如说我老家的那个县城,本来有三家电影院,现在一家变成证券市场,一家是超市,一家卖家具。不是电影无法跟大众接触,而是这个管道被切断了。再回头看看现在银幕上都是哪些人呢?中国每年生产一两百部电影,表现城市之外的普通百姓的太少太少了。说起来有些世态炎凉,今天我们走在城市里,北京上海广州,随便一个,你问问多少人跟县城、跟农民有关系?五分之三的人。大家的背景是县城,但转身,就没有人再去关心那个地区生存的人,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人道的。反过来我到有些轻视所谓城市感受,城市生活,我觉得大家既然都有农业背景,就不要装了。
问:但看你电影的时候,仍然有人说你的观点太「个人化」了。
答:其实我觉得那不是「个人化」,而是自我意识。当你作为发言者,要很真实地表达自己真心的体验,这种自我意识是艺术最珍贵的地方,也正是中国艺术里面最缺乏的。我们文化里有很糟糕的部分,不把个人当回事儿。比如我上次听报道,说这次矿难才死了两个人,这种说法太让人震惊了,才死了两个人?要死多少才够?人的事都是大事,每个个人的爱情、命运都很重要。为什幺很多年后,我们看沈从文或者张爱玲,仍然这幺热爱?因为不管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里,他们都是从私人的、个人的角度进入讲述,这是非常珍贵的。现在很多年轻导演是努力在把这样一种语感带回到我们的文化里面。但是观众可能不熟悉,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和主流思潮一致的语态,所谓「宏大叙事」。 中国观众看完电影习惯问一句,这电影说了什幺。这种归纳中心思想的训练我们从小就在进行,但其实这样对作品的单一归纳,有悖于艺术多元性的表达。观众的习惯,还需要时间慢慢改变。
问:你参加过很多国际影展,在国外的观众能理解你诠释的中国形象吗?
答:威尼斯影展一结束,《三峡好人》我们就卖了三十多个国家,为什么卖这幺好?其实背后的三峡工程并不重要,没有人会花钱只为了看看那个国家究竟怎幺样,吸引观众的一定是电影里的情感、人性,这些是共通的。《三峡好人》讲了一个离婚的故事,一个复婚的故事,两个普通的主人公通过选择,给了生活一种自由。这些经验是人类共同的,能够产生共鸣的。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太强调东西文化的冲突了,在深层的情感上,文化是有共通的,比如生、老、病,死,比如选择。
问:《三峡好人》是你第二部公映的电影,从地下导演走到现在的地上状态,对你来说变化在哪里?创作会有影响吗?
答:关键还是我得到了应有的权力。在创作上到没有什幺影响。经常会有人跟我说,你现在不要拍这个,两年后再拍,或者你现在应该立刻拍那个,会走红,但我不喜欢这个状态。我今天心里有念头要拍这个电影,干嘛要等到两年后。当然电影会有它生不逢时的时候,但是那又何妨呢?就像人不能选择它的出生,我知道现在是文革了,我不出生啊,我等结束了才出生,哈哈,那不可能。该出生就出生,那是他的命运。电影拍出来,叫好也罢,和市场有距离也罢,那也是它的命运,顺其自然。导演真的不要有太多算计,纯洁一点,天真一点。
问:这样的天真会不会带来一些困难,现实上的?
答:会有困难,现实上的。一方面是自己的,我有很多题材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非常完美的,但现在就是不想拍,现实给我的呼唤很强,总是把计划放在后头。外来的阻力就更大了,我九九年被电影总局禁拍,零三年才解禁,四年。
问:禁拍是什幺状态,真的不能拍吗?
答:可以拍,但是不能放。就算拍,状态也不会好。你知道拍电影是一个需要调动许多资源的工作,比如说我要拍这条街,我可能要封这条街,就要跟派出所和交通部门打招呼。他们问你是哪个制片厂的,你的拍摄令呢?……你是非法拍摄啊,所以很多事情都做不了,那段时间真的很痛苦。
问:那怎幺办呢?没法拍想拍的题材的时候怎幺解决呢?
答:我觉得还是想拍就拍……(笑)。大环境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,因为它很不正常,太不正常了。像今天文学和绘画基本上还能做到表达自由,但是电影很严格,甚至很多电视剧要是换成电影都根本不能拍,一定通不过。比如我看过一个电视剧写一个煤矿工人,下岗多年,发不出工资,好不容易过年发钱了,又给抢了。呵呵,这样的题材要换成电影,没人让你拍。而且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,只有青少年保护法,暴力和色情都不让拍。但如果换一个美学的角度来理解,电影作为一个大众媒介,最重要的支柱就是「暴力」和「色情」,如果没有分级制度,电影的空间太小了。
问:但是在公演的电影里,有些也能看到暴力和色情啊。(记者脑中浮现夜宴…… )
答:问题就是这里,什幺是色情,什幺是暴力,我们没有标准啊。有些电影不脱衣服也可以拍得很色情,我就能拍(笑)。色情不色情,最后还是领导说了算。现在中国在建立电影工业的体系,所有的政绩就是票房。所以商业电影受到天然的帮助,比如张艺谋的电影,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到十二套都在宣传,《英雄》公映的时候,好莱坞电影一个月不让放……呵呵,我《世界》可做不到。
问:这次你选择了香港做亚洲的首映,讲讲你对香港的印象吧。
答:我前阵子去了好几个香港的大学演讲。我一直鼓励香港的学生,你们一定要树立香港自己的文化自信。在大陆长大的人,无形中会有一种概念,所谓地大物博嘛,就说我们是华语文化的主体,这是根深蒂固的概念。但我自己跟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、东南亚有了长时间的接触之后,我真觉得没有哪个是主体,大家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华语文化的概念。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,四九年之后,在中国大陆是断的,但它还在香港、台湾延续下来。比如王家卫导演,大陆没有一个导演可以拍《花样年华》,因为那是四九年以前中国流行文化的延续,电影里的生活都是四九年前的流行生活。还有像中国的老电影《马路天使》,对人情世故、世俗生活、家长里短,那样熟练的描写,四九年之后就看不到了。我们突然变成一个单位、一个集体,家庭邻里的东西,啪,一下子断了。但是在香港还有,像尔东升的《新不了情》。我在油麻地散步,看到很多繁体字的招牌,那种亲近感真是血液里的。
2006年11月23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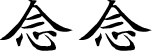
贾樟柯:最重要的不是历史,是人 已经有 3 张纸条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