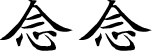尘埃落定
2006年11月11日 8 张纸条儿了已经
让我在白发还没苍苍时流浪
2006年10月17日 3 张纸条儿了已经
老兵(一)
2006年10月16日 4 张纸条儿了已经
流浪歌手·桂花·书架·街心公园
2006年10月12日 7 张纸条儿了已经
话说
2006年10月6日 3 张纸条儿了已经
懂了,就不寂寞了——不得不说的《夜宴》
2006年10月3日 2 张纸条儿了已经
心之所安即为闲
心之所安即为闲__欧阳应霁专访
2006.9.30
二零零三年开始,中国大陆的书店里开始出现一系列装帧精致的生活类书籍,《回家真好》、《半饱》、《寻常放荡》、《设计私生活》……作者记录生活里点点滴滴的智慧和技巧,文字与照片相互穿插,看似随意却极具匠心,不到一年的时间,就占据各大书店的畅销排行榜。自此,封页内一个穿白T恤的香港男人开始进入国人视野,并迅速成了年轻潮流群体推崇的生活导师。
他是欧阳应霁。雨过天晴是为霁,欧阳应霁在个人介绍里这样定位自己:“一个不甘心因此也不容易被标签定位的创作人。时而涂鸦漫画荒谬奇情一心造反,时而登堂入室访亲会友大做文章,或者驻守厨中舞刀弄叉饮饱食醉,或者离家出走天南地北浪荡终日。”
不拘一格、灵感四溢的文字和设计,成为一种独特的应霁风格。这个因为对各种生活细节和潮流孜孜以求而受到国内新兴“小资”阶层追捧,被奉为休闲生活大师的香港人,却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,“我对主流很悲观,其实休闲真的不在于去哪里,玩什么,休闲是种心灵的力量。”
你的书在中国大陆卖的很火,很多年轻人都把应霁看作他们的休闲榜样。你自己是怎么界定休闲二字的?
休闲其实是很本能的对生活的一种要求。因为忙的状态太多,所以才有休闲的需求。但如果别人觉得我是很懂休闲的人,那就真是误读了。我其实是喜欢工作的,我觉得工作要认真,要尽量做好,然后才是安心。安心的状态,就是休闲。休闲给我感觉是这样一个过程:忙忙忙……乱乱乱……然后搞定了,那一刻,那一秒,啊……是最闲的。可能下一秒,就要进行另外一个工作。每个人的休闲其实都会不同,重要的是一种态度。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强烈的目的,为了休闲而去休闲,它就反而变成一种负担,就有一点麻烦了。因为比如旅行,不一定就是快乐的,也许会遇到更多矛盾和冲突,也许并不能很放松。休闲不仅是个行为上的东西,它是个态度上的主动。
讲到休闲这两个字,说说你最先想起的三个中国人,三个中国的城市?
三个中国人。一个是我蛮欣赏的台湾画家郑在东。他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,比我大十岁左右吧,他是很典型的那种生活在现代的古人。他也喜欢游山玩水,收藏小东西啊,古玩啊,也在画画而且画卖的很好。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工作的着力点在哪里,是用玩的状态来养他工作的部分。我觉得这就是最精彩的。
另外两个人是无法真正认识的,一个是老子,另一个是林语堂。老子是中国“闲”的老祖宗了,他思想的任何一句话到了现在,都是一个独立的想法。跳过几千年是林语堂,跟我们比较靠近,我们还可以到台北的阳明山去看他的故居呢。我最近常常要上山去看他,每次去故居坐坐,心情也好。也常常反反复复看他的书。他没有张爱玲那么锐利,那么有戏剧性,但是他的生活里有一种贯通的智慧。其实林语堂一生也完成很多事情,翻译家、教育家、发明家,他发明了中文打字,还编字典……这是多忙的一个人,但他又好像是这个世纪最闲的一个人。所以他生活里头的那种张力,那种包容,我觉得简直是偶像。
不过你说哪三个中国城市让我想起休闲,我想来想去,只能想起哪三个城市不算。——杭州,成都和丽江。(记者汗。。)因为这三个城市你去到,你会太自觉要去休闲,休闲成了潮流,被模式化了,这种强烈的目的我觉得就和休闲很违背。
那闲字其实很难得。对于一个老百姓,你觉得闲,应该怎样去获得?举个例子,比如上海人工作一星期,周末选择去杭州喝茶,这个算是休闲吗?
这当然是,这是工作的一种调节。但是我觉得如果要真正去了解休闲、工作、生活,我们的状况还是太坏的。我们还是陷进在一种很浮躁、很焦虑的状态里。坏如何可以改变?我是相信革命的。这个革命要颠覆很多东西。首先是个人,你要问自己这辈子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,不一定说你把工作辞掉就是这个革命的完成。这个革命是要你改变生活的态度,甚至包括你的饮食习惯,你的衣着的选择,你住什么地方交什么朋友,完完全全很彻底。换个说法,比如你可以采取一种绿色的,新生活的状态。当然也要看各人性格决定。一说到这里,就不是大家理解的闲了,就是有一点暴烈的行为。我自己有这样的冲动不过没有这样的能力来马上进行革命,所以我觉得不如把那个能量变成自己工作上的投入,让自己现在的工作成为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。
这种革命是指,不要被生活驾驭,而去驾驭生活吗?
我也不敢说要驾驭生活,但我觉得要争取对于生活的主动权。比如97年开始我没有正式上班,以个人的身份或者很小的团队来工作,特意把自己边缘化。这个感觉好比站在舞台的边上,而不是中间。因为在边缘,你实际上就有另一个最大的空间,并且灯光暗暗的,你可以做很多离谱的事情。如果在中间那一点,大家都看着你,你也许得到最多的掌声,但是没有用,幕总是要落的。
你说要脱离主流,是因为主流会扼杀很多,让人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的“闲”?
对,因为主流是什么?主流就是利益,就是这个“$”。主流里的休闲是怎么样,是有组织有利润的,比如集体旅游,所有一切都安排好,为什么安排呢,因为有价格、利润、有交易。虽然主流是天罗地网地存在,你不可能真正逃离,但某些事可以妥协,有些部分还是可以去争取啊,还是要清楚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。我比较佩服那些尽量争取大部分时间,工作,不在主流,不在“气场”的生活。或者起码是一部分时间可以脱离“气场”,这样你可以保留创作者的独立的观点和能力。
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进入这样一种边缘状态?
和媒体访问开始。(笑)因为你问啊,我就想该怎么回答……开玩笑的,是在商业电台工作了十年之后吧。那里有很棒的同事,也是一段很精彩的时间,半个娱乐圈嘛,所以很快看到台前幕后的真真假假。看到了真实的生活,才开始问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东西,开始尝试脱离。这就是又一个十年过去了,啊,已经十年了。。再下一个十年,啊,就要退休了。。
有没有想过退休之后去哪里?不在香港吧?
不一定啊,真的不一定。我常常说对喜欢旅行的人,如果你真正懂的话,留下来,也是一个旅行。所以十年后真的一直呆在香港也不一定,因为如果你问我对香港有多了解,我会马上立刻脸红……
刚刚经过楼下的时候,我看到这里旁边有家好古老的店,以前都不会注意。
对对,如果我不在这里,可能就不知道香港有这么古老的小店。在中环这种地方,一家这么破旧的店和一对老夫妇在生存。这也是精彩的,这就是生活在里边。鸡蛋啊,什么小东西啊,我都会找个理由去那里买。跟老伯聊聊天啊,聊这样一种街区的生活,那一分钟、两分钟,你觉得自己在做一个最有意思的事情。买东西也不是为了要让他们继续可以维持下去。那个房子最后老了会倒,那个老伯老了会走,他下一代肯定不会接着下去了。但有些事情,有些东西注定有他生存的一个过程,没法强求。既然现实已经很残酷了,为什么不换一个乐观的角度去看。就像香港,我生活了几十年,但我怎么能说对这里已经认识透彻了,已经死心了?对我来说,休闲的状态,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的。家里、椅子、床都可以是最好休闲的地方。去楼下7-11也可以是一趟旅行。因为休闲的力量应该是在心里,老实说大家有时太在意环境了。
会有孤独的感觉吗?
孤独不是坏事,对我完全不是沮丧。我蛮享受孤独的时候,真的很过瘾、很开心。有时候我是故意争取自己孤独,反而担心的是,自己内心没有孤独的能力。人需要很完整才可以孤独,要有孤独的本钱,这个是需要时间反反复复积累才可能有的。很多人都在反复实践了,所以我们该看看前人记录的东西。哪怕是一厢情愿的回忆。
你最欣赏的生活态度是怎样的,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?
恩,我觉得是三点,努力工作,认识有趣的人,做有趣的事。努力是本,要从个人出发,不是为了完成别人的期许。。(此处省略200字。欧阳同学逻辑混乱中。。)
2006年10月3日 3 张纸条儿了已经
秋凉
2006年10月2日 4 张纸条儿了已经
阿傻的星期三
2006年9月14日 8 张纸条儿了已经
秋天、周末、闲扯
2006年9月10日 7 张纸条儿了已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