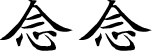君子之交
1966年文革开始,父亲已是万念俱灰。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刻怀疑的他,真的写起诗来。他一做诗,便感吃力,便想起作诗比说话还要利索的张伯驹,便要自语道:“这对夫妇如今安在?怕也要吃苦受罪了。”父亲的诗,绝句为多,都是信手写来。树上的麻雀,窗外的细雨,炉上的药罐,外孙的手指,他都拿来入诗,惟独不写政治。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,由政治而荣,因政治而辱,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。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伤,还是该向他祝贺?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,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他走时,我正关押在四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。一年后,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、四川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,从宽处理: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。狱中产下一女,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。苗溪茶场地跨天(全)芦(山)宝(兴)三县。那里与我同在的,还有一个在押犯人,她叫梅志(胡风夫人)。我站在茶园,遥望大雪山,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。十年后,我丈夫走了,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被宣布:无罪释放。宣读时,我无喜无悲,宣读后,我面对一纸裁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,拒不说感谢之类的话。因为我觉得是他们长期亏待了我,有什么可感激的?我穿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裤,回到北京。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慢慢移出,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,亲睹我的丑陋憔悴,吓得躲在我姐姐背后,别人拖也拖不出来。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,也为欢迎我回归故里,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的“东来顺”,吃的是涮羊肉。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,红红亮亮规规正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磁盘里。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。看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至友的兴奋面孔,我很想说点什么,但我什么也说不出;至少我该笑一笑,可我也笑不出。幸亏在亲友当中有个老公安,他以极富经验的口吻,低声解释道:“关久了刚被放出来的人,都不会说笑。以后会好的。”谢谢他的理解,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。我的那双红漆木筷,千百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。我一个人干了六盘,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。“小愚吃了一斤八两(老秤说法)!”不知谁报出了数字。这个数字把全场震了,也让我笑了,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。我想,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,还有我的母亲。可扭脸一看,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的滴滴老泪,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,纹丝未动。这一夜,母亲和我和我女儿三代,共眠于一张硬榻。女儿上床后便昏然大睡。我与母亲,夜深不寐。这一夜,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。我问的第一件事,就是父亲的死。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,我都死死记住,记到我死。母亲告诉我:首先得知死讯的,是梁漱溟和张申府。那日,父亲死在了北京人民医院。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,走到西四的时候,便碰上了迎面走来的梁、张二人。在街头,他俩问道:“伯钧现在怎么样了?”母亲说:“他去世了,刚刚走的。”张申府,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,一道漂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,满脸凄怆,低头无语。梁漱溟,这个同我爸一起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号,又先后被民盟摒弃在外的人,伫立良久。尔后,梁公说:“也好,免得伯钧受苦。”接着,母亲又告诉我:父亲死后,她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恳请搬家。好不容易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间一套的单元房。……母亲说:“自搬到建国门,我就清静了,谁都不知道新地址。可是,你能猜想得到吗?是谁第一个来看我?”我从亲戚系列里,说了一长串名字。母亲说,不是他们。我从“农工”系列里,挑了几个名字。母亲说,不是他们。我从民盟系列里,拣了几个名字。母亲说,不是他们。我说:“如果这些人,都不是的话,那我就实在想不出,还有谁能来咱们家呢?”“我想你是猜不到的,就连我也没想到。那天下午,我一个人在家,拣米准备焖晚饭。忽听咚咚敲门声,我的心缩紧了。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地址,找上门来打砸抢。我提心吊胆地问:‘谁?’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:‘这里,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?’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,我一点也不熟悉。忙问:‘你是谁?’门外人回答:‘我是潘素,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。’我赶紧把门一开,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,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。我更没有想到的是,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。几年不见,老人家身体已不如从前了,头发都白了。脚上的布鞋,满是泥和土。为了看我,从地安门到建国门,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。”听到这里,我猛地从床上坐起,只觉一股热血直冲胸膛——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,悲恸欲绝。《易经》上说:伤在外者,必返其家。一家骨肉,往往也相守以死,而我却不能。狱中十年,我曾一千遍地想:父亲凄苦而死,母亲悲苦无告。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,看上一眼?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,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?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,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。如今,我一万遍地问: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,到底有着多少分量?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;不过是看看画,吃吃饭,聊聊天而已。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?他怎能和父亲的那些共同患难的战友相比?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、关照与接济的人相比?人心鄙夷,世情益乖。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,似流星坠逝,如浮云飘散。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,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门,向远去的亡灵,送上一片哀思,向持守的生者,递来抚慰与同情。母亲又说: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,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时间长。母亲要沏茶,潘素不让,说,“伯驹看到你,便放心了。我们坐坐就走,还要赶路。”张伯驹对母亲说:“对伯钧先生的去世,我非常悲痛。我虽不懂政治,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。他不以荣辱待己,不以成败论人。自己本已不幸,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,是个大丈夫。所以,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。现在又听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,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。早先,对身处困境的袁克定,凭着个人能力还能帮上忙。今天,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,自己已是有心无力。”“张先生,快莫说这些。伯钧相识遍天下,逝后的慰问者,你们夫妇是第一人。此情此义,重过黄金。伯钧地下有知,当感激涕零。”话说到此,母亲已是泪流满面。……母亲的叙述,令我心潮难平。政治吞没人,尤其像中国的各种运动,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,因人的硬度而不等。当然,知识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。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,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优游态度、闲逸情调、仗义作风、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人性与独立意志。他以此抗拒着政治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。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,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,过着他那份生活。张伯钧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。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,就是他的一颗心,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。
2006年9月8日 3 张纸条儿了已经
往事并不如烟——储安平(摘)
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;大家拥护党,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。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,推行它的政策。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,巩固已得的政权,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,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,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。但是在全国范围内,不论大小单位,甚至一个科一个组,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,事无巨细,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,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。这样的做法,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?
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,但跟党走,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、政策正确,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,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。这几年来,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。没有做好工作,而使国家受到损害,又不能使人心服,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,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。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,党这样做,是不是‘莫非王土’那样的思想,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。我认为,这个‘党天下’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。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。”
“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,党群关系的不好,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。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,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,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?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。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。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,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。”
“解放以前,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。1949年开国以后,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,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,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。可是后来政府改组,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,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,他们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。这且不说,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,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,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?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?从团结党外人士,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,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,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?”
“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,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。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,但是处理得当,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。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。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。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,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,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,毕竟有限度,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,党群关系怎样协调,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,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,更以德治人,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,这些问题,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。”
2006年9月5日 一张纸条儿了已经
梦境一种
从恒温二十度的地铁站冲进空调坏了的小巴,我湿淋淋的脑袋正和眼镜一样,一片糊涂,熟悉的音乐突然就劈头盖脸地砸进眼前白茫茫的世界里……
我不是有意要写得这么后现代,只是发生的一切都实在有点戏剧化。
我从来没有在香港遇上过空调坏了的小巴。
我从来没有在香港的小巴车上听见过音乐。
我从来没有在香港,任何的公共场所,听到这样的旋律——
“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,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。我要飞得更高,飞得更高,狂风一样,舞蹈挣脱怀抱……”
世界在汪峰的声音里一片朦胧,不真实得让人想流泪。
我蜷进车尾的角落,闭上眼睛,央求这声音不要停,不要停。
我看见镜头里那个叫嫣芳的年轻女孩,她慢慢地说,我十六岁一个人到北京,背着吉他,带着三十块钱,晚上不知道去哪里。我在地道里看到一个男人弹吉他,就在他身边坐下来,我坐了很久,听他唱完一首又一首歌,然后我们开始聊天。后来他给我一百块钱,让我回家。他说,你还小,不要在北京流浪。我没有听,我一直留了下来。
我听见这个不美丽的女孩子,昂起脸,倔强地唱,我要飞得更高,飞得更高,狂风一样,舞蹈挣脱怀抱……
我听见她弹吉他,微笑着,唱自己写的歌词,《谁会在乎》:“你们这个世界认为的好,我不要。”
我记得她的声音很坚硬,在高音的地方,用力地唱,一直唱到沙哑。
我听见唐朝乐队的国际歌,我听见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,我听见郑智化的年轻时代,我听见各自放纵的KTV里,那些熟悉的面孔唱着破碎的梦想,掷地有声。
我看见月黑风高的夜晚,在青草和啤酒里,和他们,她们,调侃爱情,戏谑诗歌,欲拒还迎地讨论理想。
窗外的世界重新清晰,巨大的广告牌幅从四面压来,内衣明星搔首弄姿,极尽妖媚之能事;路人甲乙丙丁花枝招展,香气扑鼻,整齐地排列在红绿灯两边。斑马线旁不知疲倦地响着“嘀-嘀-嘀-嘀”或“嘀嘀嘀嘀”的声音,提醒人们随时保持秩序,随时紧跟效率。
2006年8月25日 4 张纸条儿了已经
学习抖包袱
2006年8月23日 一张纸条儿了已经
漂泊
2006年8月22日 4 张纸条儿了已经
搬家@自然卷
周末,把自己扔进阿麦书房和无印良品,在喧闹的铜锣湾竟然独享安静地泡了两个下午。
发觉自己开始愈发变态地买书,和迷恋MUJI的东西了……
在阿麦书房听到很好听的背景男声,当即买回了那张CD,原来是《自然卷》,台湾一个年轻的非主流组合。环绕在安静书房里的声音是奇哥,一首在台北搬家的故事,却让我听到了香港的味道。
呵呵,境由心生……
搬家@自然卷 主唱:奇哥
三箱的CD 两箱的玩具
四箱的书 半箱的秘密
发黄的墙壁
刮花的磨石地 年轮的回忆
怎么整理 在士林的五坪里晾着内衣
楼下的7-11是营养补给
呼吸着不怎么新鲜的空气
不知不觉 门上贴了个喜
We Are Family
Are we moving moving moving moving To a place with free
Are we moving moving moving moving To a place without lonely
I wish
凋零的市区 奢侈的郊区
骄傲的闹区 游戏的学区
钢筋水泥的台北丛林
生存下来需要一点勇气
搬离一个半成品
搬到下一次累积
两百公里外的妈咪
依然等着我
不是不想回去
觉得有点来不及
I am moving moving moving moving
To a place with free
I am moving moving moving moving
To a place without lonely
I wanna go home
Which one could be the one
I am still moving moving moving moving
To a place with free
I am still moving moving moving moving
To a place without lonely ……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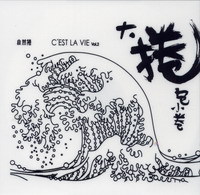 <自然卷>乐队第二张专集,“大卷包小卷”,但现在乐队已经解散…
<自然卷>乐队第二张专集,“大卷包小卷”,但现在乐队已经解散…
2006年8月13日 3 张纸条儿了已经
远离真相的世界
必须承认,石头的确好看,手法耳目一新(对中国观众而言),幽默得很本土,故事讲得很机灵。大笑完了之后,还能让人心里稍微回荡些什么。小市民的小炎凉,讨了观众的欢心,也赚了大把笑声和银子。就像超女一样,邻家小姑娘在舞台上放声歌唱,她鼓着勇气的样子很容易让观众心疼。但是小姑娘真能像柯阿姨说的,“拯救流行乐坛”吗?一部有那么点灵气的小电影,真的成了“中国电影的希望”了?石头好看,但,有“那么”好看吗?
石头再好看,也是甜点,不是主菜。呼声那么高,是因为中国电影观众在对主菜的等待上,饥饿太久了。
超女再流行,也是娱乐,不是音乐。选票那么多,是因为大家在主旋律里“高雅”太久了,急需“低俗”一回。
同样地,郭敬明再畅销,也是文字,不是文学。粉丝那么多,是因为今天文学的粗制滥造,让孩子们根本模糊了两者的界线。
我们可以夸奖甜点做得好,娱乐得快活,文字得情调。但是把文字当文学,把甜点当主菜,心满意足地说我们被拯救了,我们有希望了,这不是挺悲哀的一件事情吗。
媒体挣扎在竞争的压力下,不停制造标新立异的概念和危言耸听的结论,拼命抓住眼球,抓住市场。看客虚荣在五光十色的信息里,脚步紧跟,口径一致,生怕一不留神,潮流的快车就从眼皮下开走了。这边厢,“有良知”的媒体愤青抱怨自己必须“跟大众市场妥协”;那边厢,“被忽悠”的广大观众集体声讨媒体“浮躁低俗”。
保持清醒,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在今天,大家都急于做出点什么,表现点什么的中国,尤其不容易。而我们,似乎正合力营造一种离心力,让世界,和它真实的样子,渐渐远离。。
衷心希望,这些,只是我的危言耸听。
2006年8月9日 7 张纸条儿了已经
若若安归来
2006年8月8日 3 张纸条儿了已经
三万英尺随想
这是在飞机上完成的一篇博客。尽管完成它的工作是纸、是笔,但似乎我已经开始习惯把这样零散的文字或是日记统称为博客了。博客的概念,公开不公开,早就不是个问题。木姐姐爽过了,竹姐姐脱过了,芙姐姐糟蹋过了,各路明星也一齐出马,在博客江湖里厮杀的天昏地暗了。平凡如我辈,即便拼上老命某某横陈,求爷爷告奶奶地漏点隐私,估计也没几个人有功夫在意。所以,就这么一写了,还是那句老话:每日一博,健康生活~~(我用了一个月再博,绝对亚健康。。)
说说这趟飞机,深圳航空,波音737小型,ZH9558,目的地:无锡。在广州机场时,好不兴奋地给大陆同胞发短信:“张小平中国移动版今日诞生,有效截至7月30日。”算上刚在广州霍霍掉的一个多星期,这是自从到HK以来,我最长的一个假期了,三十天,而且合情合法——可不是我逃避工作,呵呵,我是被特区政府驱逐的……此前,还跟好友一本正经地商量怎么纪念这被驱逐的日子,说旅游,说西北,说内蒙,说云南,说的豪情满怀心有戚戚。如今,朋友毫无悬念地踏上唧唧复唧唧的工作之路,我也急不可耐地爬上回家的飞机。只有在那个“被遗忘”的博客上,我眼巴巴地看着,一些和我们一样的平凡人,怎样选择了我们没有勇气抑或幸运去实现的流浪梦想。
我不认识夏。在space上,他的居住地址是香格里拉。夏的MSN的名字里有个521,猜想必也是个重情之人。他的思想沉重而轻灵,他的笔触热烈而冷默。他用荒唐形容自己,他选择远方告别,或者实现青春,他用安魂曲伴随流浪。夏说:“人們不需要智慧,好比曾經擺在路邊,沒有畫框的凡高的畫,從來沒有真正的藝術過。”夏说:“孤单,要么颓废占据我身,要么坚强进入我心,我渴望后者。”
我完全不了解这个人,也不想用我们所说的“奇迹”去妄加评论一个也许坚强也许脆弱也许只是平凡的灵魂。只是,我仍然敬佩这样的选择,以及它背后,必然的决绝和勇气。 香港特区告诉我,8月1日签约正式工作。从此我与“学生”这个词彻底告别。朋友恭喜我:终于把自己卖掉了。我心里说: 没有,是我终于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。
想起那天,在海琴湾27楼落地玻璃窗前的谈话。 Z抱着公仔坐在窗帘后的角落里,盯着前方广州百分之一概率的碧水蓝天珠江景,说,“冒险让我觉得快乐,做好了实业的基础后,也许我会不断投资、投资。”眼里,亮光闪烁。 Andy面对的是一排排江景豪宅,眉头微锁,“我不能有太多风险,我希望我的事业是稳定的、可预见的、慢慢的进步。这年代生活不易,希望我的孩子能过好日子就行了。” 我站在他们中间,看两个本是轻狂年纪的年轻人理性的计划,低调的语气,和眼里隐藏的光彩(或者杀气:p),忽然觉得,其实站在这个所谓的分岔路口,我们仍然清楚地看到了自由,把握了机会,也准备了承担责任。
夏选择在香格里拉半隐半读,Z选择从他热爱的cisco开始,Andy选择进入体制内,改造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。而我从旁看着,在满足中,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——一个旁观的身份,一个冷静的视角,一颗能被感动的、热情的心,和一点尽力而为的改变。
常常想我们这些人,五年后是什么样子,十年后又是什么样子。今天努力计划的一切,实现了多少?今天意气风发的梦想,剩下了几何?但其实不重要,真的不重要,今天我真心地为这班朋友自豪,相信明天也是一样。因为重要的,不是结果。重要的是我们梦想了,努力了,然后认真经历着粗糙生活的一切,失败也罢,成功也罢,真正收获的,都在心里。
飞机终于开始降落。从三万英尺的高空,俯身看到的这个夜间城市,是我从来不能想象的,最壮美的景色。
遍地星光,遍地传说。
很快,我将要汇成它们中微小的一点,和朋友们各安一方,再难有交集。但让我们都努力、努力地发光吧,也许从天上看,我们之间曲折的微光,恰恰是个美丽的星座呢?
…………
2006年7月22日 3 张纸条儿了已经
ENGLISH CORNER
2006年6月26日 9 张纸条儿了已经